2月23日,习近平在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部署会议中特别指出,“要发挥社会工作的专业优势,支持广大社工、义工和志愿者开展心理疏导、情绪支持、保障支持等服务”。
今天,一名身处武汉疫情风暴中心的社工老师——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院任敏,来分享她作为亲历者的所见所闻所思。从她的分享中,我们来看看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社工该如何发挥专业优势。
在过去一段时间里,笔者常常接到外面各界同仁的电话,问情况如何,我们社工是怎么做的,难题在哪儿,经验有哪些,对未来社工发展的启示,以及外面的人通过网络收集数据来问询我某些数据该如何理解等。在多次内外“通话”中,笔者都能感受到内外部人认知之间存在鸿沟。这也促使笔者意识到一个城内人(所谓城内人、城外人并非地理概念,“城内人”是指深度参与疫情救助工作的人,“城外人”是指限于各种条件无法或没有深度参与疫情救助工作的人)应有责任来促进内外沟通。本文试图就前期的一些认知差异集中点做一些表达,以回馈大家对武汉的关注和帮助。
总体来说,笔者经历疫情时期关于专业认知有几点深刻体会:第一,非常时期不同于平常时期,平常时期的规范难以直接搬用。非常时期的专业行动需要历经实践并从中开展研究,总结、抽象而来。第二,过去两月的武汉战“疫”,有两个突出的情境性特点:时间上处于传染病疫情爆发期,空间上具有政府全面管控特征。理解情境性对于理解城内行动十分重要。第三,在行动中始终要伴随深刻反思,与同仁之间交流、澄清,同行求知。
1.依据什么专业原则行动?
依据什么原则行动是我们在疫情救助中常问的一个问题。
2月中旬,笔者有学生进入隔离点服务组做线上服务,很快遭遇一个难题——案主给学生提出来“你能帮我联系住院吗”。这是学生服务中经常遇到的问题,怎么办,怎么回答?在非常受挫亦不知所措的情况下,笔者组织学生们在线讨论。有人指出:“告诉老人们我们只是学生,有些事情我们是做不到的,但是我能做到的是每天来陪你聊聊天”,也有人提出一个问题:“对于我们做不到的事情,我们是一开始就拒绝不给对方希望好呢,还是我们给他希望,而后来让他失望更受打击好?” 学生们得出的结论是:“还是一开始就拒绝,讲清楚边界好,免得后面案主失望反而打击更大。”
笔者对此做了督导工作, 建议学生们:“案主们已绝望地等待多天了,这时需要输入希望,如果是我,会有不同的处置法,说‘是啊,床位的问题太难了,我也真是没有把握能否帮您争取到一个床位,但我们可以一起去尝试。我听说微博肺炎超话上发帖子求助的,平均5-6天可以获得床位,那么我们明天开始把您的求助信息发布上去,接下来几天广为发布……对了,信息发布要规范,我们一起来整理,而且听说有社工志愿者专门帮忙整理求助帖子,更规范的帖子获得关注的可能性更高,我们来琢磨下 ……’而5、6天过去了,很可能方舱开放更多,社区就可以安排床位了呢?而如果还没有,那我们就说,‘现在中央很重视,人民日报也开辟了渠道,听说3-4天就可能有回应了,我们继续尝试下,我们不放弃,坚持就有希望……’如果我们跟案主一起行动,带着希望,加上每日陪伴,撑过十天,那时候自然就有床位了。”
为什么会如此说?我的理解是,之前学生们讨论的原则都是对的,但是那适用于平时稳定环境。在稳定环境里,今天不能解决的问题,明天、后天往往也不能解决,一切是高度可预期的,所以,我们在工作中直接划定界限说我不能做到这点,可能没问题,但现在是非常时期,情况每天都在变。2月4日,武汉开始有方舱医院开仓,且还在陆续开放,这些都是资源;2月10日下达“应收尽收”的指令,纵然是实施需要时间,那也不过晚些天的事。而当时已2月15日了。但一般的案主,尤其是文化资源和信息通达度不高的老人在困顿情况下可能认知不到位,所以那时候不要去掐灭案主看见新来一批帮助者而升起来的希望的小火花。
这个案例说明非常时期不适用于平时的工作原则, 我们需要情境化地去处理问题。而且这显然也跟同学们对情境认知不足,是跟他们刚参与救援、缺乏涉入“深度”有一定关系,而这也正是他们成长的机会。
2.“线上+线下”服务模式创新?
这个模式从一开始就有城外社工同仁与笔者电话讨论过,认为这当是本次疫情期间社会工作行动的一个创新之举。
但大家都提得简约,“线上+线下”的主语究竟是谁?各人所指不同,各色各样,比如有些人理解“社工线上+服务对象线下”,有的理解为“社工(团队)线上+志愿者线下”。而比较多的社工同仁理解为“社工(包括机构)线上+社工(包括机构)线下”联动,其中社工也指社工管理的志愿服务团队,即包括医心志愿力量;这能理解,因为我们就是社工。但如果认为是“社工线上+社工线下”,这需要做点澄清。
这与其说是现在已有做法的经验总结,不如说是预期未来我们将去施行的一个做法。而如果它成立的话,也主要是我们社工在后期获得参与行动合法权后,服务于“隔离点“这么一个短时期内的过渡性做法。准确些说,目前存在“社工(团队)线上+志愿者线下”联动模式。即使个别社工参与线下也基本是分散“志愿者化”了。
原因有以下两点:
一是前期传染病疫情爆发期间,各行各业的行动都要听从国家的统一部署,在没有行动合法权、防护物资奇缺的情况下,社工是出不去的。而且也没有哪个社工机构敢于承担感染风险把社工派到线下去工作。武汉市的岗位社工少,所以社工嵌入在社区行动体系去行动的也少。这时是有个别社工自发去做志愿活动,但实际上我们是难以社工的名义去行动的。
二是当后期风险降低了,我们就恢复平常时期的工作模式了。而我们平常时期的模式,自从有了在线沟通技术和工具以来,我们一直都是“线下+线上”模式运行的。比如一个社工一周去探访某案主老人一次,那么非探访时期当然随时是可以通过“线上”来保持联系的。
总体来说,截至3月中旬,这次武汉的社工参与服务基本只是“线上”,这是由行动是否有合法性以及传染病疫情的阶段性特征决定的。但诚实地讲,我们在不能出门的情况下,在没有谁动员我们的情况下,我们并没有“安居一隅”“岁月静好”,而是想尽办法,可以说我们不少人都没日没夜地自发投身线上的抗疫工作,这本身就非常值得肯定!体力参与重要,脑力参与也重要;一线服务重要,而资源链接、政策倡导、督导培训、社会倡导等这些工作都很重要,甚至结合疫情爆发期的需求和抗疫特点而言,这些工作更加重要。我们不必要因为无法第一时间以社工的名义参与“线下”做服务,实现令人振奋的“社工线上+社工线下”联动,就妄自菲薄。非令、无组织、不乱动,在非常时期,这其实是服从抗疫大局的做法。
这种提法内含的创新之处和重要意义,于这次的抗疫经验而言,其实并不在于“社工双线“联动,而在于强调当“线下”不能行动时,我们可以通过“线上”行动,线上工作同样是有成效和有价值的,而且我们可以总结具体的线上行动模式。但总结模式并及时推广也可能内含一个悖论,一方面模式总是具有简化和固化的内涵,以便于识别和传播;另一方面在全新情况下,一种新模式的迅速传播会引发“抄作业效应”,即大家都倾向拿来即用,这反而会压抑社工在具体情境中创造性解决问题的动力。一个可以克服“抄作业效应”的方式是引入行动研究,即以开放的心态保持反思,在行动中朝着如何实现更好的服务目的而不断地讨论、改进。
据笔者所知,武汉本地社工一边在积极地推广这些线上服务群模式,如“4+1”模式等,另一些人也在反思超越,积极探索新的实践经验,比如强调“一一对接的责任人”方式,以及看似被动的“应需才动”在针对具体不同人群的服务中可能更适用。基于对各类服务方式的观察,笔者认为,我们的研究也许更需要深入地去追问一些细致的问题,比如 “线上”服务中,大群、小群各自的功能是什么,服务是采取大群、小群、个案方式,还是大群加小群,还是大群+个案方式,依据什么服务场域而定,什么样的案主群体特征而定,以及不同的场所和对象服务方式固然不同,但是又有何相同等。
尽管目前的经验不支撑这种模式,但这个概念却非常好地激发了我们的想象力,而且正是这种想象力与经验之间的差距使得我们可以进一步去探索,何以这次不行,未来什么条件下可以实施,从而为未来的工作做好准备。这也凸显了“线上”服务的重要性及其可探索性,让我们探索“线上”与“线下”服务的区别与关联,以及促进信息技术在服务中的应用研究。
3.社工“牛”在哪儿?
有几个城外社工界同仁打电话跟我说,你们武汉社工好牛啊,比如你们激发了“社区+物业”分工抗疫模式。这背后折射的是城外人对武汉社工在非常时期迅速协调行政和市场力量行动的高期待,但认知需要客观,应该说武汉的社工角色发展还尚待时日。这种事情若发生当属极个别特殊情况,缺乏总体基础。
在疫情时期,“社区+物业”分工抗疫模式应该主要是社区工作力量在响应上级的任务和回应居民期待中彼此协调形成的,很多社区不论有没有社工参与,都在这样做。在没有这样做的社区,社工可以建议他们这样做。但总的来说,社工不太可能“牛”到主导社区居委会和物业去干什么,因为我们不是他们的领导,没有资源,可以让他们“听”我们的,这没有组织基础,不合逻辑;而且尤其是在任务压力超负载的当前状况下。社会中很多精英,我们社工的角色就是发现、激发精英、协调各方资源来行动,应该说很多时候我们在行动中恰恰是要淡化自身的“精英”色彩的。但疫情时期,即使我们社工没有激发或说主导社区和物业去创造一种合作模式,如果身体力行地参与协助他们工作,无论是线下还是线上,这本身就是非常有意义的。据笔者所知,有些社工就是以志愿者的形式参与社区送菜送患者之类,协助社区和物业工作,这本身就非常值得称赞。
此外,在疫情爆发期这种特殊情境下,最重要的抗疫力量是医护人员和政府系统,而社会工作者没有合法性进行系统介入的时候,我们就只是作为带社工印记的志愿者深入各个空间参与其中。如果非要区分我们跟普通志愿者的区别,可以说是我们很多行为都是“有意识而为之”的,且带“技术含量”的。比如据笔者观察,疫情期间,在一些大群里,如果出现人群言语冲突了,社工们就会“跳”出来,作为社会工作者,我们会随时随地自觉地去承担协调者,促进人群相互理解和社会融合的那个角色。而且这些时候,说什么话,怎么说,我们都是带有理论考量的。
在疫情期间,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院的学生们一直积极倡导做“行走的社工”,即随时随地、随情随境地按照社工的价值、用社工的技术去待人做事。社工通常并不占据丰富的组织资源,也并不都是精英,所以在权力和能力意义上我们很难说多“牛”,比如在链接资源方面,相信有很多活动能力强的志愿者比我们“牛”多了。当然那也是我们的努力方向,但目前我们“牛”在我们有深切的价值关怀,一直被训练以人为本,主动参与,“自觉”行动,促进社会公义、和谐与健康。
笔者坦陈,作为身处武汉疫情重灾区的一名社会工作老师,具有“教师+社工”双重身份,在疫情之初内心十分焦躁,那时眼看着只有医护人员和政府人员、志愿者在行动、能行动,而作为所谓专业社工的我们基本被困家中,似乎什么都帮不上,跟很多同工一样,一时之间我的专业认同焦虑被激惹起来,常常自我怀疑。但所幸笔者反思很快,从专业自证的焦虑中摆脱出来,认识到此时重要的根本不是任何人、任何群体的自我证明,而是以抗击疫情为中心,投入救援、认清形势、摸准需求,有效、高效地去促进各个群体的需求得到满足,问题得以解决,那才是/就是我们要做的。我也认识到,至于什么样的行动才凸显专业性,面对全新情况,专业行动是在行动中变得专业的。那么首当其冲的是立足现实,参与进去,然后在参与中保持思考、持续反思、交流讨论,在行动中求知,经过行动得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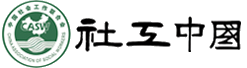













已有0人发表了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