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家乡意义的消解
滕尼斯意义上的“社区”是一种人际关系层面的生活共同体,其特点是亲密无间、相互信任、守望相助以及拥有共同的信仰和风俗习惯,而农村则是滕尼斯“社区”一词所指的典型态。按照滕氏对社区的定义,农村作为一种典型社区,对于生活在“陌生人社会”之中的社会成员无疑充满着魅惑力,也容易由此勾起出走乡村进入“陌生人社会”的游子的浓浓乡愁。然而,遭受着现代化冲击的乡村似乎已经开始慢慢地淡褪了原来守望相助的关系色彩,而在“经济理性下乡”和“劳动伦理变迁”的浪潮下变得摇摇欲坠。淳朴的乡村由此涂上了一层理性的灰色,家乡一词被解构成了家与乡两个独立的单位。对于离乡的游子而言,寄托自身情感的只有家却无乡,乡的概念逐渐变得模糊(在一些人心目中,有家无乡),对乡的归属感大打折扣,乡愁俨然成了家愁的代名词。而对于在乡的人们而言,乡村也或许更多地只是指涉一个地域,而不是原来那个亲密无间的共同体了。
一、劳动的商品化
市场观念在乡民脑海中的扎根,一方面在某种程度上突破了传统观念的束缚,为乡民致富提供了理念上的准备,而在另一方面,则冲击了传统的以劳动交换劳动的互助模式,使得劳动力变成可直接用货币进行购买的商品。而劳动力的商品化对乡村较为纯粹和传统的人际关系来说,缺失了传统互助模式中在劳动交换之外的情感沟通功能。因为,传统的劳动交换劳动过程实质上是存在于乡村中的一种互助模式,是其守望相助的表征,或者也可说是一种极为朴素和广义的交换。此时的“交换”可以是直接表现为农忙时候的合作,也可以表现为在该村庄内部某一户或某几户出现劳动力紧缺(比如某户人家在举办婚丧嫁娶相关活动的时候,需要大量的人手来协同进行)的时候,邻居将劳动以人情或不计回报的方式赠送给彼此,而这种付出也必将在之后得到“没有预谋的回报”。在这个劳动交换劳动的过程中,并不因为一次劳动交换的结束而终结,而是以类似于人情循环似的方式绵延下去。而在劳动商品化之后,村庄(社区)成员劳动直接表现为可供购买的商品,支撑劳动付出的不是之前的人情原则,而是表现为市场化的交易逻辑。这种方式,一方面增加了货币在社区内部流通的频率,且让闲暇劳动力资源相对富足的农户和个人有了一个新的增收渠道,并在一定程度上吸收了部分剩余劳动力,使得其“在乡就业”成为可能;另一方面,则失去了劳动交换的绵延性以及蕴含在交换之中的情感功能,出卖劳动的一方很少再将自身的劳动行为视作是一种帮助或奉献,购买劳动的一方也不再将对方看成是人情主体,而只是认为自己购买了对方的服务。这样的劳动商品化交换在双方的心理层面都被认定为市场交易,“花钱买服务”的逻辑似乎无论从哪个角度看上去都理所当然。
劳动的商品化替代劳动交换劳动的互助模式,不只是交换形式上的改变,更从性质上改变了这种交换,原本的“交换”是不带或者很少带有经济利益的广义交换,而现在的交换更多的是商品经济意义上的“生产—购买”。交换性质的改变弱化了乡民之间的情感维系力和整个乡村的凝聚力,缩小了互助的范围,乡村间的互助减少(更多的是商品交易),只有家庭这一生产单位还保有着原来的风貌。长此以往,乡村的人际关系遭到削弱,加之劳动力的向外输入和地域之间的发展差异,依靠人际关系纽带而让离乡人产生乡愁的重要变量缺失,或者因为进城失败等因素而寄望于外出务工获得收入,然后回到家乡成为“老板”购买他人的劳动,不论是继续农业生产还是回到农村创业均是如此(这与后文所提到的“消遣伦理”相应和)。这样,对于背井离乡的游子来说,产生乡愁的原因不再是让人神往地亲密无间的乡村,寄托自身乡愁的单位往往不再是乡而是家。
二、微观视角下三种劳动伦理的影响
陈柏峰在《去道德化的乡村世界》中指出:“20世纪以来,中国农民生产的组织形式和相关经济态度经历了从消遣经济到劳动经济,再到消费经济的转变,每一次变化,其背后都有特定的劳动与财富伦理的支撑。”在他看来,消遣经济时代人们将闲暇和不劳而获看成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劳动经济时代的人们将劳动视作一种责任和荣耀,消费经济时代“高消费”和时尚成为了人们追逐的对象,并认为当下中国农民正日益受到消费经济的影响。不得不说,从劳动伦理的角度来看待农民的经济态度是一个很好的角度。笔者认为,通过劳动伦理这一解释性框架,还可以分析目前存在于农村的其他问题,譬如因赌博事件引发的肢体冲突,以及在其原本意义上解释农村中的“炫耀性消费”或“符号性消费”。
笔者家乡在湖北B村,应该算一个典型的贫困村。从劳动伦理的角度来看,笔者发现,消遣经济、劳动经济和消费经济三种经济态度在家乡的村落中同时存在,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个体的认知和选择,但从年轻一代来看(或许这反映了一种趋势),越来越受到消遣经济和消费经济的影响,这也似乎在说明三种伦理并非是一种单线的“进化”。在B村,老一辈农民更加认同劳动伦理,就如费老(费孝通)所说的“农闲时也依旧劳作”,农忙的时候自然不用多说,他们几乎会依据自身所能承受的“极限劳动力度”来度过这段时间,农闲时或者遇上不宜劳作(下雨天等)的时间则会用“手工”来“打发时间”,男性以木工和编织(这些人多继承了“篾匠“的手艺)为主,女性则以织毛衣、做布鞋等为主。那些颐养天年的老人每天主要的时间花费在晒太阳、串门聊天等事项上,不过这些人并不会得到来自于“农闲依然劳作”阶层更多的艳羡,年老体弱无法劳作被看成是无用的象征(对于有劳动能力但家庭条件较好的人则不同)。年青一代也有人信奉消遣经济的劳动伦理,他们主要依靠短时间外出务工(集中在煤炭开采和炼钢等职业)获得收入或者靠在附近村落出卖劳动力为生,平时多聚在一起“打麻将”来消遣,也正是因为牌桌上容易产生纠纷而将这些纠纷移植到日常生活中来(当然,牌桌生活似乎已经成为其日常生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产生肢体冲突,继续破坏乡村的和谐。应该说,有相当一部分人信奉消费经济,“修楼房、买小车”成为很多人的追求,本来,向往更好的生活无可厚非,但在完成这些炫耀性消费、符号性消费有时甚至是冲动性消费后,很多人缺少了抵御未来不可预期风险的能力。
消费经济造成了乡村的盲目攀比以及由此带来的“红眼病”(从笔者的经验来看,这种现象的确存在),“红眼病”的存在容易促使乡民在看似微不足道的利益点上发生矛盾甚至冲突,劳动伦理的代际差异为一部分人继续自己的“啃老事业”提供了空间,消遣经济则给乡村的和谐安定构成了挑战。
一个案例:
近些年,H君与Z君在笔者家乡当地可谓名人,一个是以狠劲儿闻名,一个则是因为在生意上敢闯敢做而受人尊敬。乍看上去,二人并无太大的可能滋生矛盾。然事实是,此二人皆痴迷于赌桌,混迹于“赌圈”。他们之间的矛盾也便是由此而来:Z君在牌桌上赢了约莫万元,碍于情面或处于义气,退还了一半有余给对方,而H君则不依,并当场放下狠话。随后,H君带两车人感到Z君家中,一通乱砸乱打,Z君也有力的给予H君以还击。
此案例是笔者在8月份回到家乡的真实见闻。在这个案例中,H君与Z君由于不直接从事农业生产,Z君虽然在当地创业,但除了刚开始筹划较为繁忙之外,平日闲暇较多,拥有较多的“闲暇时间”,且都遵循“消遣经济”伦理。这种消遣至少在笔者家乡的人们看上去是值得羡慕的,因此构成了村落中“虚假的有闲阶级”(如陈柏峰所指的“另一种有闲阶级”)。从农业生产中抽离出来获得更多的闲暇时间,但这些闲暇时间并非全然用来从事非农生产,加之农村业余活动的贫乏、农民精神生活的贫困以及其他个体性因素,“牌桌生活”便成为了其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牌桌上涉及到很多经济利益的纠纷,并往往因为输者一方的不服气引起肢体冲突。这些冲突除了直接危害乡村的安定团结之外,还具有重要的传播功能,它向其他乡民传递出一种暴力信号(通过口耳相传让更多人的知晓这一信息),从而可能造成暴力意识的扩散(当然,另一方面会让其他乡民采取更为谨慎和保守的策略,因人而异)。而这无疑又是对乡村秩序和乡村人际关联的进一步破坏。通讯手段的发达也使得这种消息对离乡人来说并非是秘密,从而使得离乡人对家乡的印象更为负面,影响了他们对家乡的归属感。因而,对于很多人来说,随着归属感的降低,家乡里只有家却没有了乡。(作者:山东大学社会工作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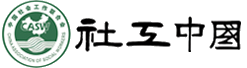













已有0人发表了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