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和CCP利用驻村做到了不同的事,为讨论驻村的意义提供了最重要的案例。在我看来,驻村最突出的必要性在于:一,达到对村庄和村民的深度理解;二,关注村里的弱势群体,培育村民组织。而这跟我的两个基本信念有关:一,只有深度理解才能为我们的行动提供持久的动力、正确的方向和方法;二,弱势群体只有组织起来,以互助合作的力量改造现存权力关系和经济形式,才能改变其边缘位置。
“理解”的三层境界
理解村民很难吗?以我个人经验来说,确实如此。我们每个人都习惯用自己的逻辑去解释对方的言行,比如看到村民砍树,我们可能会觉得村民没有环保意识。这就称不上“理解”,只是给村民贴标签,把村民硬套进自己的刻板认识里。在这样的认识下,我们的行动很容易犯方向性错误,按自己的逻辑去走。
常人所谓“理解”,至少要能够将心比心:如果我是他/她,我会怎么样?这就接近社工专业中的“同理心”,意指社工能设身处地地站在对方的角度思考问题,理解对方的想法和感受。这才能算初步的理解。我们能够理解到村民砍树可能是因为生活困难、又没有别的副业收入,砍树对他们来说可能是最简单的选择。我们也可能体会到,村民急着要用钱时的那种急迫和无助,以及冒着被林业站拘禁的风险砍树时的紧张。这样我们就会更加理解村民的言行,至少我们不会再轻易地将问题的标签贴在村民身上,而是明白村民有自己的逻辑,这些逻辑在某种程度上是可以理解的——假如我们是村民,我们也很有可能跟村民做出一样的选择。这种同理,也会帮助我们建立和村民的情感连接,让我们跟得上村民的喜怒哀乐,使我们萌发想要帮助村民、改善现状的冲动。绿耕人张和清老师将这种“心动”的状态称为具备了“社区实践的感受力”。这往往是我们投身社工或公益行业的最初冲动,也是支撑我们不断前行的动力。这种情感连接,有可能促使我们走出单纯的助人者的角色,进而可能与村民建构一种协同行动、相伴同行的关系模式。
但“同理心”一般运用于个案工作中,偏重对对方的情绪、想法和感受的同理。这种微观层面的同理如果没有“社会学的想象力”的指引,就不能使我们理解到村民言行和情绪背后的社会性根源。我们可能还是局限于一些微观或中观的层面,比如个人、家庭或者社区层面。我们即使想要行动起来改变现状,也只会强调这些微观或中观层面的改变,其本质是推动个体对大环境的功能性适应。
“社会学的想象力”的关键,就是将我们的私人生活、个人困境以及成就等均视为个人置身的特定时代和特定社会结构的折射。这样我们才能看到,个别村民家庭的入不敷出与宏观的社会政策或社会结构有什么关系,比如,是否受到医改的影响(个别家庭因病致贫与国家医疗保障体制的关系)?是否与消费主义有关(个体消费增长与整个社会消费主义盛行的关系)?很可能我们会看到,导致村民砍树的问题是整个中国的农民都面临的问题(比如贫困),这个问题的形成有其历史脉络和社会结构的成因,只不过在某些地方我们看到的现象是砍树,在另外一些地方则是挖矿。这样我们就会明白,针对单纯的“砍树”或“挖矿”现象做环保行动是无法回应村民的问题的。我们应该以在地化的行动、指向社会性根源的改变,比如,以社区经济改善村民生计、使村民不再依赖砍树或挖矿,最终回应消费主义等问题。只有将个人的经验与社会历史事件联系起来,找到了微观现象背后的结构性原因,我们才算是真正理解了村庄和村民的处境,对村民既有感性的情感连接,也有理性的社会结构与历史的分析;既清楚我们自己为何而行动,更清楚行动的方向和方法,从“心动”走向“行动”。
“理解”的过程中最美好、也最难得的层面,即是从彼此身上看到希望、彼此激发和鼓舞、甚至照见自己。如果说,“可怜人必有可恨之处”是常见的从个体、负面层面去解释苦难的说法,那么,我们倡导的正是从结构的/外在的、正面的角度去理解苦难,比如: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下生活,确实很苦,但这他们/她们并非自身的原因,何况,过这样的生活也一定要有超过常人的劳动和智慧啊!正是因为从个体层面的“同理心”走到了“社会学的想象力”,我们才能发现,结构中的个体是如此地在劫难逃和无奈;而又正是因为无奈但又不甘的个体在结构中的挣扎和不放弃,才折射出自下而上撼动结构的希望。这样的情况特别发生在,这些个体组织起来、以互助合作去改变自己的命运的时候。
以驻村达致深度理解
“理解”并不容易,而没有深度理解,就不会有行动的动力、正确的方向和方法。说了这么多对“理解”的理解,那,对农村工作者来说,如何实现“理解”的一步步深化?一个字:驻村!这也是“社会学的想象力”指引下的“同理心”,对我们提出的要求:真正进入村庄和村民所处的生态系统中,从他们/她们的位置来感同身受、体会结构中的无奈、设想可能的出路。
首先,实现“同理”,就意味着要与村民建立有足够厚度的关系,我们必然一起经历过许多情景,一起哭过笑过,享受过共同的喜悦、痛过彼此的痛,才能形成情感连接和深度理解。而这就要依靠驻村、与村民“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才能做到。关系的厚度起码来自时间的长度,一面之交、如何能够敞开心扉讲述彼此的生命故事?在走马观花式的“下乡”中,互动的双方都是带着各自的光环(比如“有资源的人”、“想要资源的人”等)、只看到对方最外显(也是最符合自己逻辑)的角色(“项目官员”、“村长”、“村庄弱势人群”等),形成的关系就类似于契约式的工作关系,谈何深度理解?
其次,只有驻村,我们才有可能弄明白村庄的来龙去脉(尤其是村庄内部的权力结构)。任何一个村庄和社区,都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具有一定的封闭性。不驻村,就意味着我们无法进入村民的日常生活世界,不能触摸村庄运作的内部脉络,因此获得的资料就可能是零散的、片面的、甚至是被村民有意无意加工过的。这种情况下的所谓“理解”,很可能是带有偏见的。比如村中各种组织的关系,表面看分成村委会、村小组和教会,井然有序;但实际可能所有组织都被村里两大姓把控、暗斗不止;而具体原因、历史脉络和对社区的影响,又要过了更长时间(往往是项目摔了一个大跟头)我们才能知晓和理解。
最后,只有驻村,我们才能充分体认到社会结构和历史事件在村庄留下的印记,并通过这些印记去理解村民个体与社会历史的关联,进而对“大历史”、“大结构”中的小村庄或“小人物”有更深的理解(比如城乡二元结构背景下自杀的独居老人或候鸟般外出又回乡的青年)。比如绿耕,遵循“发展”的视角,意味着我们应该对以下方面有充分的评估:在这个小村庄里,发展主义的在地实践形态;发展主义实践在本地造成了何种文化、政经和生态后果;并在此评估的基础上探讨重建村民主体性、实践农村另类发展的可能性与具体方法。
我一直不太相信通过一套工具(比如PRA)就可以在短期内理解村庄和村民。驻村所保障的“理解”的深度,主要体现在时间的长度和关系的厚度。没有长时间的扎根和互动,就不能形成有厚度的关系,就达不到深度理解,就难以有持久的行动动力、正确的行动方向和方法。工具可以协助我们理解,但工具无法代替驻村,无法代替时间、关系和情感。而这些元素,是在做人的工作时必不可少的。
在“驻村”中辨识社区弱势群体
从这篇文章的第一部分开始,我就一直罗里吧嗦,说驻村是为了行动。让我们回到CCP的蹲点方法论所提出的问题:我们为谁服务?怎样服务?我们也得问自己,去农村为谁服务?我们如何为他们/她们提供服务?
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就导致了社会组织之间的细(ben)微(zhi)区别。在绿耕大部分的论述和实践中,我们是为村庄弱势人群服务的,比如绿耕的宗旨中清晰地讲了“培力弱势”。对许多组织(尤其是打着社工旗号的)来说,应该把关注弱势作为基本的价值观之一。虽然这是组织的自我定位问题,但接下来的讨论却是以此基本价值观为前提的。我们集中讨论如何在行动层面落实这个基本价值观,涉及到以下两个具体的问题:一,如何辨识村庄弱势人群;二,如何服务弱势人群。而对这里所讲的“弱势群体”,先作一个粗糙的界定:权力关系中的无权者、弱势和边缘群体,经济方面的贫困者、生活困难者。
在农村社区中辨识村庄弱势人群,主要要靠我们自己来完成。很简单,就像CCP进村,不会向地主打听谁是贫雇农,因为视角根本不一样,地主看到的是有偏差的。我们刚刚进入一个社区,最容易接触到的不是弱势群体,反而是社区里的强人,他们/她们在最好的地段盖了最漂亮的房子,也活跃在社区的公共舞台上,在各种场合都容易见到其身影。他们/她们代理着社区各种事务,尤其是跟外界(比如我们这些外人)对接的时候。弱势群体,尤其在农村,本身往往就是地理位置上的边缘者,他们/她们住在山上或角落,大部分时间在田地里干活或在家里忙忙碌碌,一般不会出现在“做代表”的场合里。他们/她们往往是被代表的,除非有个场合特意召唤他们/她们,比如PRA。
面对这样的情况,我们可以借助基层政府或学校的各种花名册,但真正的辨识和落实社区里的弱势群体,我们只有靠自己亲自去走村子、去家访、去做具体的调查和分析。“隐形的”、“被代表的”弱势群体,是要“挖”出来的。因此,如果不是特别坚持“关注弱势”的价值观,我们其实是很容易被打发、然后自己也觉得满足的。
我们一定要主动打破已经固定的权力关系格局,放下身段、积极地走社区,让社区里的人接纳我们,为社区弱势群体开放心理和关系上的空间;我们要主动转换活动的场所,走到社区边缘的山顶或角落,进入平民老百姓的家里面;我们要主动参加社区里的活动和聚会,进入村民的日常生活和生产的现场,了解他们/她们在具体的生产生活中碰到了什么难题。这没有什么高深的技术和方法,对我来说,只有最基本的态度的要求。所以我特别强调“主动”和“参与”。这个“参与”,不是单向的弱势群体来参与我们的活动,我们更要去参与他们/她们的生产生活;我们希望影响和改变他们/她们,那么首先我们要开放一个空间,让他们/她们可以影响和改变我们——至少这样才能发生对话。当我们有了这样的视角和态度,驻村就是自然而然的选择。
这件事,CCP做得很科学。他们以阶级分析作为基本的框架和划分方法,很快就能辨识出一个村里的不同人群。而且,他们能够以极其强势的宣传和政治工作,打破村庄固有的权力关系,营造弱势群体“当家做主”的氛围,进行快速的发动和组织。在这个过程中,许多细致的工作都是通过“蹲点”来完成的,特别是通过村里自有的党员或积极分子(因此省去了很多前期建立关系和了解的时间)。
对绿耕来说,其实比较简单,一方面我们通过排除法来确定项目不以哪些人群为主体,另一方面,我们要求工作员尽量掌握整个社区和所有村民的情况。因此,这个辨识和了解的过程是贯穿于项目始终的。
长期驻村,与村民组织相伴同行
如何服务弱势人群?我们认为培育组织是最基本的策略,弱势群体只有组织起来,以互助合作的力量改造现存权力关系和经济形式,才能改变其边缘位置。在培育组织的过程中,我们就可以将可持续发展、自助互助、能力建设等理念落到实处。
培育组织大致可以分成“前期发动”、“相伴同行与组织成型”、“关系转化与组织独立运作”三个阶段。特别是在前两个阶段,培育组织只有通过驻村才能完成。在外部工作者介入、协助弱势群体组织起来、改变现状的情境中,工作者需要以驻村的形式陪伴村民组织成长、以能力建设支持组织、以合适的协作者身份强化弱势群体的主体性。以下主要讨论前两个阶段。
“前期发动”大概是指,在辨识弱势群体之后,通过个别或小组性的谈话、会议与讨论,明确他们/她们的兴趣与资源,一起制定共同的蓝图,并确认只有通过互助合作、组织起来才能实现该蓝图(有合作和组织的意愿)。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可以明白,上述“辨识弱势群体”的过程就不只是了解情况、落实名单这么简单了。所有的互动过程都至少包括深化理解和动员/发动两个层面。对驻村的工作者来说,行动是连续的,是从“初见”到最后“分手”的持续流动。我们需要辨识这个流动的过程中的关键点或转折点,以便及时地转换角色或工作策略,但不会人为地将其分成独立的工作程序。
在“前期发动”的阶段,因为工作者与社区弱势群体双方正处于发展关系、建立信任、达成共识、磨合节奏的关键时期,所以,只有通过长时间的驻村不断巩固、趁热打铁,才能真正发动社区弱势群体。尤其在考虑到以下两个方面时,驻村就显得更加必要和重要:
一,长期处于边缘地位和权力弱势、且本身有很重的生活压力的弱势群体,在谈及资源、改变和未来的时候,或许不会有充分的自信,或许在过程中会出现犹疑与波动。这个时候尤其需要工作者以耐心和细致的工作去协助弱势群体重建自信,而不能自己代替村民冲上前。好比CCP进村跟贫雇农说要斗地主,尽管大家平时受尽欺压、有很强的动力,但说真要打土豪、分田地,心里都没底。这时候,工作者可能要通过小规模试验、介绍其他地方的经验、反复的聚会与讨论等方法,甚至(举个极端例子)像《让子弹飞》中先从名义上杀了黄老爷,才能让平民百姓真的有信心去参与。
二,很多组织的工作者(至少绿耕是这样的)发起的项目,有可能会涉及到:一,改变参与者的生产生活习惯(比如从常规种植转为生态种植);二,触动社区现存的权力格局(比如弱化社区强人的参与、侧重考虑弱势群体);三,需要大家共同参与、以行动去创造一个新的事业(比如开展城乡互动),实际上也要求参与者共同面对不确定的未来。参与这样的项目,换成我们自己,也会走一步看一步,何况那些跟我们交情还不一定很深、而且会在当地永久居住的(因此这些项目的成败对他们/她们来说会具有完全不一样的、我们可能无法领会的意义)村民?
在前期发动之后,我们可能找到了社区里的一些弱势群体,他们/她们成为项目的积极分子,参与制定了项目的规划并认可蓝图,也愿意投入时间和精力、以合作的形式来行动。把这些积极分子聚集起来,再共同确认大家的想法,并进入具体的行动计划、合作分工等方面的讨论,这大概就是组织的雏形了,马上要实际行动了。从此开始的很长时间里,工作者要和这个刚刚培育出来的小组一起去面对很多挑战,并不断通过各种形式的能力建设提升组员的信心和能力,推动组员走出来承担他们/她们自己的事务。这个过程大概可以称为是“相伴同行与组织成型”,其中“相伴同行”就是指工作者的角色。
组织的过程大概会碰到两大方面的挑战:
一是组织本身的运作。主要指组织如何形成顺利运作的机制,包括带头人和组织骨干的培育、组织制度的形成(组员都认同的规章制度、很具体的分工协作等)、组织的合法化(从自发建立的小组到取得合法身份的组织)、组织的公共关系处理(跟社区其他组织、政府及外部合作伙伴等的关系)等方面。
二是组织所开展的项目或行动。主要是指组织所做的事如何能做成,并不断扩大覆盖面、可持续运作下去,包括一件事情从无到有、再到好的过程中所面临的生产、包装宣传、市场销售等方面的问题。
大多数时候开局并不难,但要持续做下去就会面临诸多挑战。不管是组织运作还是项目行动,都是如此,只要我们干的不是一锤子买卖(比如基建类项目)。所以,这些事情都可谓是没有终点的。终点要回到“人”,人若成长起来,工作者的角色就可以暂告一段落。工作者的“相伴同行”,就体现在以协作者的身份,和组织共同面对这些挑战,最终使“人”能成长起来。
因为我们选择了从弱势群体出发,而他们/她们在面对组织运作、项目行动等方面的挑战的时候,确实需要足够的时间去学习;特别是面临新事情的时候(比如跟外界对接、领导一个组织或集体决策等),因为过去在生活中锻炼的机会可能不多,所以他们/她们可能比社区强人需要的时间更多、在某个阶段的进展可能更慢;特别是在触碰到社区现存权力格局的时候,他们/她们可能会需要工作者的一点点助力。但我一直相信,在合作方面,他们/她们一定会更有基础(越是觉得自己有能力的人,往往越难真正投入到合作的关系里面)。这样的“组织”的过程,其实是一项“慢工出细活”的工作,就像歌里唱的:“慢慢来,会比较快。”只有通过驻村的“慢工”,在日常的互动中彼此打通疑虑、澄清想法、仔细掂量,才能使“组织”顺利起来;也只有通过驻村的“细活”,才能让组织成员慢慢进入节奏、重建信心、敢于承担,避免工作者喧宾夺主的情况。通过缓慢但不间断的前进,这些组织起来的平民百姓,最终能成为社区和发展的主体。在这个过程中,工作者的长期相伴同行就显得不可或缺,或许某些时候还要“添一把柴”。
毛泽东说,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就群众的组织而言,我想他有些时候还是急了一些,虽然朝夕必争,但也要做好持久战的准备。因为我们怀抱的是这样的信念:如果一个社区的弱者能够组织起来、自下而上的改造局部的社会现状,那么整个社会的改变的希望和路径就是清晰的。我们需要的只是时间。
到这里,清晰地意识到这些是集体的智慧了。比如讨论组织的很多内容是来自绿耕从化农村社会工作项目。但许多表述是个人化的,还需要推敲。
另外,关于“理解”的部分,多处参考了张和清老师的《知行合一:我的社会工作行动研究历程》一文,未一一标注。
文中有个逻辑问题是没有讲明白的,即:“关注弱势群体”就一定以“培育弱势群体的组织”入手吗?可能会有人问,跟强人合作会不会也有相同效果?我觉得这个问题掰开来讲清楚也有点复杂,怕影响主线就先不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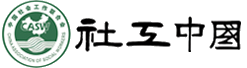













已有0人发表了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