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社会治理创新后,如何推进社会工作参与社会组织建设和社会治理,进而提升其在社会治理创新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成为社会工作学界研究的焦点议题。除针对当前专业性教育和实务经验的研究外,中国社会工作学科史研究近些年对反思社会工作本土化优势亦提供了不少历史经验。但是有关社会工作学科史的研究方法尚未得到系统讨论,而这一研究工作对能否建立学科史与当代学科实践之间的有机联系,对能否在当前学科话语体系之外拓展学科的本土化理论内涵均具有重要意义。
综观当前中国社会工作学科史研究方法,不外乎学科起源研究、学科专业性历史定位研究两种思路。前者从专业知识的生成史角度,一方面探讨了中国社会工作发展与西方社会工作传入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则从内生性历史角度出发,检讨这一现代学科与清末民初中国社会思想与社会运动之间的关系;后者则以社会工作理论的专业性内涵为标准,来辨析社会工作作为现代社会科学学科的起源,试图将前一种研究中掺杂的那一内生性历史视角从专业性学科范式中排除出去。这两类研究争论的逻辑,颇类似于20世纪冯友兰与胡适之间的“哲学史”写作之争,虽各有理据,也皆失其偏颇。学科的生成史研究分离了中国传统社会思想与社会工作作为现代知识体系之间的关系,因而未能呈现前者向后者转化的内在逻辑;与之相对,立足于专业性理论范式的学科考辩,又将中国思想与社会传统资源拒于现代学科范式之外,由此无法开掘出有助于形成公共性伦理品格的中国传统社会给养,难以实现学科理论的扎根化。两种研究思路的偏颇,皆可归因于忽略了对近现代中国社会科学学科生成的“问题域”的关注,因而难以形成有关学科起源和发展的总体性研究方法。
20世纪前叶历史社会学初兴之时,有关“起源”问题的历史研究引发不少论争。“年鉴学派”第一代学者马克·布洛赫等人曾就“起源的迷惑”批评了两种历史研究倾向:其一是为现实政治和意识形态寻找历史的辩护辞;其二是缘于“判断癖”,为考证而考证。两者都是“真历史”的死敌。换言之,若不能廓清历史事件背后绵长且动态的社会结构演变,便不能理解偶然历史的必然性。可见,某一学科在知识发展史上的出现,作为一种表面上的偶发历史,仍需回到知识谱系生成的总体性、结构性历史中界定其本性。在此意义上,知识的生成史是思想史和社会史交叉影响的后果。这既不能以辨析学科专业成立的事件标志代替学科生成的内在历史逻辑,也不能用专业知识范式的当代标准来抹杀知识发展过程中的历史丰富性。为把握这一知识生产的发展脉络,中长时段的历史分析视角显得颇为重要,有助于在三个层面上突破既有的中国社会工作学科史研究方法的壁垒。
首先,总体性历史视域中的学科史研究蕴含着比较历史分析的眼光,有助于我们在中国近现代社会转型的“问题域”中理解中国社会工作学科兴起在中国社会治理议题转变中的必然性。诚如孔飞力、杜赞奇等人对清末民初地方自治问题研究所表明的,以“绅董”集团为代表的地方社会崛起,使晚近中国国家治理陷入了困境:一方面体现在地方社会与国家力量的竞争,另一方面则体现在国家通过行政吸纳社会的方式维持体制稳定。可以说,这一治理结构奠定了整个20世纪中国国家政治的基础。在此过程中,如何锻造能够适应现代中国的公民道德,对于突破这一治理逻辑的“收放”循环具有关键意义。这就意味着,在现代国家治理体系下,已经不能完全借助传统经史之学来应对这一社会条件之变,包括社会工作在内的现代社会科学的兴起是在新兴条件之下回应社会变迁议题的必然趋势。社会工作学科发轫伊始如何理解这一近现代中国社会转型议题,如何在政治建制过程中呼应公共性伦理和道德建设的历史使命,皆构成社会工作参与社会治理创新的知识基础。
其次,总体性历史视域的学科史研究也意味着将社会工作学科视为知识谱系加以系统整理,而不是以当前的学科专业分类眼光将其肢解,从而为中国社会工作的理论本土化创新提供契机。尽管20世纪初中国教会大学社工系的成立借助了西方社会工作学者的力量,但早期中国学者并未照搬外来知识,而是在回应上述历史命题中摸索适用于中国特有民情与社情的理论和实践模式。比如,燕京大学社会工作传统扬弃了当时美国社工界侧重个案工作的主张,将个案工作、小组工作整合到社区工作体系中,通过改造中国传统的乡约思想,并结合区域理论研究带动社区工作发展,走出了一条独特的社会建设实践道路。特别是清河试验倡导的综合性区域经济体建设、协调城乡平衡发展的思路,对于今天农村工作和农村政策稳定农村经济发展,锻造自我生长的农村居民群体仍具有启发意义。
最后,总体性学科史研究方法还需在“集体行动”层面上廓清学科实践的行动基础,即将社会工作学科发展置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社会运动中,考察不同知识学派和实践行动的关系,从而理解这门学科在中国文明语境中的精神本质。如果跳出专业性视角来看,早期社会工作学科实践仅构成了乡村建设中的部分流派。它对于转型中国建制议题的回应是在学派之间思想论辩以及实践合作中逐步确立的,因而,理解这些论辩和实践模式之间的异同,既对于澄清社会工作本土化理论形态的复杂性极为重要,同时对于捕捉纷杂的知识形式背后的统一的文化价值亦十分必要。知识分子作为这一社会运动的担纲者,将“回到民间去”视为对被腐蚀了的世道人心的挽救,其本身即构成了反思建构现代中国公共伦理品格的重要维度。
诚如王思斌所指出的,中国社会工作史研究是对中国社会工作历史品格的把握,换言之,也是对知识的典范价值的书写。由古知今,并不意味着孕育在历史中的知识可以直接转化为工具性效用,相反,只有在“古”与“今”既有差别又有现实联系的前提下,知识的典范价值才能构成对当前经验反思的意义。因此,仅为好古的起源考证,或仅以当前效用为目的阐释,均不足以呈现一门学科精神的运化在整个时代流变中那跌宕起伏而又一以贯之的轨迹,而这正是总体性学科史研究的目标。
(作者单位:中国政法大学社会学院;北京大学学科建设办公室)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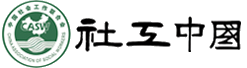













已有0人发表了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