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任文启 甘肃政法大学)
新冠疫情爆发以来,社会工作专业力量在教育界和实务界的共同组织下,迅速汇聚成一支庞大的行动力量进入抗疫一线,开展线下防控与线上支持,为抗击疫情做出贡献。习近平总书记“2.23”讲话之后给社会工作专业注入了一剂强心针,社会工作教育和实务界一方面深入学习讲话精神,另一方面继续躬身抗疫一线尽社会工作专业的微薄之力。虽然前不久吴世友、何雪松等学者在公共卫生社会工作的范畴内谈论疫情中的社会工作专业定位,但目前总体的防疫工作依然还是以行政体制为主导的“国家动员”模式,社会工作专业力量在这种模式下不论是“嵌入”、“汇入”,还是“融入”,在效果上都是一样的,均是国家动员的各种力量范畴内的一枚螺丝钉,也均需要在国家动员的框架和逻辑下进行的。
国家动员的特征,简言之就是“集中力量办大事”。“集中力量”即可以举全国之力,在物资资源、医护力量、管控布防等方面实行国家调配,比如全国优势资源挺近鄂中,医护力量分批次驰援湖北,“一省包一县”等,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的体现。“办大事”即国家可以迅速有效地回应最紧迫、最重大的群众关切,解决最关键、最核心的社会问题。国家动员的核心是“自上而下”的“体制主导”。所谓自上而下,就是站在国家或国际层面考虑全局,逐级制定方案、安排部署和遵照执行。所谓体制主导,就如大家所看到的,动员的主体以行政官员、党政干部、军队医护等体制内力量为代表,动员的方式是命令式和行政激励式的,比如“多长时间内没有实现何种防控目标就要撤换行政负责人”,“考核干部要看此次抗议过程中的实际表现”,“有危险任务党员优先”,“境外返回人员集中隔离收治”等等。国家动员在此次抗疫中是有效的,是结构性力量,是值得肯定的,这也是一贯的体制优势。社会工作力量参加抗疫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进入语境的。
就具体行动而言,抗疫开始之后,我们听从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统一安排,组成了一个由社会工作师和心理咨询师牵头的社区抗疫督导团队(作为八个督导组中的一个),对口支援湖北黄冈。在与社区工作人员共同面对基层抗疫的实际问题时,我们感受到了基层治理方面的问题,比如:国家物资可以有效达到湖北,这些物资如何迅速、有效地分配到每位抗疫战线的工作人员手中?各社区需要救助、隔离、检测的人员如何有效对接到医疗资源?以及到社区防控的严控阶段,如何使居民的基本生活得到保障?居民有多样的生活需求,又如何通过行政管控得以满足?国家的每一个数据都来自社区,社区工作人员每天的表格都填不完,这些数据如何保证真实有效?基层的工作人员的核心任务究竟有哪些?所有的任务中,孰先孰后?孰轻孰重?就基层的社区工作人员而言,除了薪水、专业、资源和任务面临压力之外,还有诸如职业暴露、行政考核、体力透支、心力俱疲等问题,均在此次抗疫行动中纷纷呈现出来。我们也看到报道,此次抗疫过程中,已经有53名社区工作人员付出了宝贵的生命,这53个因公殉职的社区工作人员身后,不仅有53个家庭,更有成千上万个面临同样问题的基层社区工作人员。由此抗疫看出,越是顶层的国家动员,就越对基层治理能力提出更高挑战,平时“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到了防疫的关键时期,基层不仅“压力山大”更是真的都在“拼命”。
同时,国家动员可以保证在全局上不出问题,但国家动员的方式深入到基层之后,尤其与老百姓直接对接之后,就难免不在微观层面出现问题。比如,防控志愿者为了防止“聚众”而到老百姓家里砸了一家三口娱乐的麻将桌,这虽然是志愿者越权的一种举动,但也是行政命令执行一刀切的产物。前不久武汉某业主群里流出的“大妈汉骂”中能更真切地感受到基层社区的需求:基层动员如何开展?是只完成自上而下的命令、任务和表格就行?还是需要瞄准居民需求、回应居民需要、组织居民自助、促进社区自治?
凡有问题处,皆是入手点。我们习惯了“自上而下”的“体制主导”,反向上就会强调“自下而上”的“行政辅助”,也就是说,社会工作力量参与抗疫开始,我们的定位除了自上而下地传递政策、信息与支持之外,就是自下而上地将居民的问题呈现出来,将居民的需求反映上去,将这些问题和需求写成改进方案和策略,上报镇市政府,再由他们出面制定政策和文件,做到“上下贯通”,这也是社会工作参与社会治理的一贯逻辑。但我们很快就发现,一是基层社区工作人员压力太大,他们的实际问题是对上只有命令和执行,对下又有居民的抱怨和不满,我们的建议和支持只是为他们提供更多的策略而无法有效解决这些问题;二是我们的意见与建议一旦进入文山会海的行政流程,他们到底有没有机会去看到和听取则是要打上问号的。更关键的问题在于:我们从一个助人者的设定角色演变为一个能看清问题的旁观者和改变不了问题的建议者。简言之,在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行动机制下,社工在“上下贯通”之外,还应该寻求更为切合实际需求、促进细节改观的行动空间。
如何寻求新的行动空间?换一个分析框架就能清晰看到社会工作专业应该关注什么。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其实是国家动员的两个方面,即便没有社会工作专业的介入,上下的信息也可以通过社区以行政的方式予以传递。我们更要看到“自上而上”和“自下而下”两个方面的行动空间。所谓“自上而上”即是顶层设计的问题,比如十九大以来的社会治理现代化,就是自上而上的构想,能够在顶层把需要关注的方面都设计到,这是体制机制自我改革的路径。社工界之所以对习近平总书记“2.23”讲话产生热烈反响,也是希望社工能在“自上而上”的顶层设计上解决社工在国家福利传递中的合法身份和有效地位。如果顶层设计不解决社工的处境,我们就可能流为积极努力的补充力量,而无法开展主体性的有效行动。所谓“自下而下”,则是从基层需求出发、动员基层自治解决基层问题,在基层形成需求-问题-解决的闭环,促进基层治理的有效。
对社会工作而言,经常会提到一个“最后一公里”甚至“最后一米”的问题,这就是指当自上而下的信息传递到基层时,如何有效将其目标在基层得以实现,依靠传统的行政主导会出现“科层失灵”的困境,比如动员社会自组织的力量,释放社会个体自我行动的意愿和能力,从基层到基层,让居民活跃起来,以居民自身的方式对接国家需要,回应自身需求,不论是个案、小组或者社区等方式,开发志愿者、培育自组织、培养社区领袖、激发自力更生热情,让基层社区力量能够有序组织动员起来,才是社会工作专业的特长所在。当然,国家动员的诸多资源,如何被识别、划分、对接以及分配使用,这些都在社工服务的技术范畴之内,也是“自下而下”行动空间的国家保障。
同时,国家动员追求的是宏观正义的问题,即病毒传染是否得到有效控制,人民的生命财产能否得到有效保护,行政在成本上的考虑则可能是“不惜一切代价”,但到了基层社区,到了每个家庭,甚至每个个体身上,宏观正义上的“不惜一切代价”就可能使个体、家庭乃至某一社区付出巨大代价。社会工作号称追求“社会正义的实现”,在国家动员的框架下,宏观正义是社会工作提供服务的总方向和总目标,但在服务每一个个体、家庭、社区时,社工需要面对每一个个体的情感、需求、心理、行动,乃至对其生命的关怀,这就是对于微观正义的恪守和追求。同时,微观正义的落地还包括:社区所动员的每一位志愿者的行动如何是合情合理合法有效的?社区自组织如何能够对接国家需要社区居民需求又可以自行其是?每一位居民的个性化需求如何得到最大程度的满足?居民自助的同时又能达到助人的效果?等等问题,这些都是国家动员“尺之所短”,也正好是社会工作开展社区服务的“寸之所长”。通过对“自下而下”和“微观正义”的行动空间的侧重与开拓,我们希望通过此次抗击疫情的社会行动,不仅厘清社会工作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功能和定位,更清楚目前基层社会距离治理的现代化水平还有多远的路要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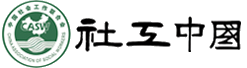













已有0人发表了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