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三,机构未把政府额外拨款全数用作调整员工薪金。
如果抑制得当,丧失的旧体制优势是可以承受的,扭曲的利益关系是可以扭转的。笔者建议,加大对机构的规制,建立经济杠杆和黑名单制度,使得他们的利益诉求回归到合理的范围,不以牺牲社工薪酬福利换取机构的发展。运用经济杠杆的时候,筹划“削峰平谷”性质的财政预备金和储备金,十分必要,以应对经济不景气年度的公共之需。
(4)改革的代价属于非战略层面的阶段性产物,代价升级是可控的
前述的“四个代价”,矛盾集中在机构董事会(股东)和政府执行者之间,或者经纪人化,或者侵蚀专业定位,或者诱发内部信任断裂,或者产生招标不公平,均属于执行层的问题。储备金的功能被扭曲,各方各执一词,源于受助机构的不当行为,属于操作层的问题。后经社署默认,转化为执行层的问题。但储备金的主要功能没有异化,仍然是保障新政持续运转的财力基础。既然战略层面没有问题,判断代价升级可能性显得十分重要。社署早在2002年发出了《领导你的非政府机构——机构管治》的参考指引,并在廉政公署的协助下,于2003年发出了5件反贪指引,如《非政府机构合约的批出和管理》、《非政府机构存货管理》、《非政府机构的人事管理》等。为提高机构管治能力,开展了系列培训,发放了定向补助款,2007年还派发了刊物《在转变时刻中领导非政府机构——启思集》。这些措施基本保障了政府资金运作的透明、公平、有序,有效预防了贪污事件的发生,使得市民对社工界的信用保持良性。但由于若干环节的执行操作不当,改革新政走了弯路,表层是收入分配机制出错,深层是磨合期的新政抗压力脆弱。为增强新政的抗压力,阻止改革代价升级,港府除了采取前述的“放水”、“扶小”等财政措施外,还采取了一系列技术措施,强化政府与机构、机构与社工之间的沟通与互信。如社署招标文件评分比重公开制、社署解释整笔拨款方法制、机构财政困难通报制、机构财政预算列明社工薪酬制、机构投标文书咨询员工制等。
事实上,改革的代价还不止于改革本身,因现存制度与改革新政之间不匹配,推动了改革风险的形成,也应计入改革代价。港府的自我修复力扩展到了改革之外,大大减轻了对新政的冲击力。具体地说,因奖券基金资助制度与整笔拨款津助新政不匹配,产生了改革以外的财务压力,诱发了机构充当了赢利性经纪人。这个压力是指奖券基金资助项目规定了大额补助金的下限(欲购家具及设备每项金额须超过10万元,欲购大型翻新工程的金额须超过50万元)和机构整体补助金占经常性拨款的上限为1%,使得项目维修费用缺口难以支付,只好由整笔拨款津助额支付,从而挤占了前线社工应付薪酬款。或者推迟这两项业务直至累计金额超过下限,才申报补助。为减轻新政推行的阻力,社署将家具和设备购置补助金的下限调减为5万元,将整体补助金比例上限调增为1.5%。
(5)政府与利益攸关方保持常态对话机制与改革的阻力成反比
改革前,整笔拨款津助制度取得了各方共识,所以改革初期进展顺利,几乎没有阻力。改革中,港府与机构之间沟通不畅。比如,机构认为整笔拨款计算方法不透明,政府所拨款额不足以应付现实需要。又如政府与机构对公开招投标的认识分歧,机构认为提交建议书和竞争性投标的过程有失公平。再如,机构认为政府受理投诉的机构不独立,社署与整笔拨款津助督导委员会均不合适。由于沟通不畅,政府与机构之间的不信任增加了,机构不能够很好履行对社工的付薪责任,政府的招标行为受到质疑。政府却未能及时发现这些信息,未能有效预防群体性事件的发生,改革遭遇群体抗议。罢工事件发生后,新组建的整笔拨款独立检讨委员会开放了4条沟通渠道:提交书面意见、会面、出席研讨会(论坛)、出席听证会,听取了相关团体、机构董事会(股东)、服务使用者、社工和市民等各方意见。于2008年12月形成了36条书面意见,直接向劳工及福利局局长报告,所提意见全部被采纳。罢工事件距今已有3年多,社工界发展比较平稳,在职人数增长了9.7%,社工平均年资增长了0.7年,离职率下降了19%[6]。这充分说明,港府在罢工事件后采取的措施相当有效。可见,常态对话机制是取得改革共识的关键,是有效预警改革风险的保障。如果改革是在没有取得共识、没有充分预警信息的情况下进行,风险和代价将成倍增加。
综上所述,改革的方向是正确的,利益分配的基本面呈良性,改革的症结与风险已经找到,政策利益攸关方保持常态对话机制,改革者建立了自我修复机制并愿意支付改革的成本,有了这五个条件,笔者认为,改革的代价是可控的,改革不会滑向陷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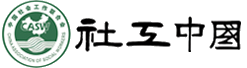













已有0人发表了评论